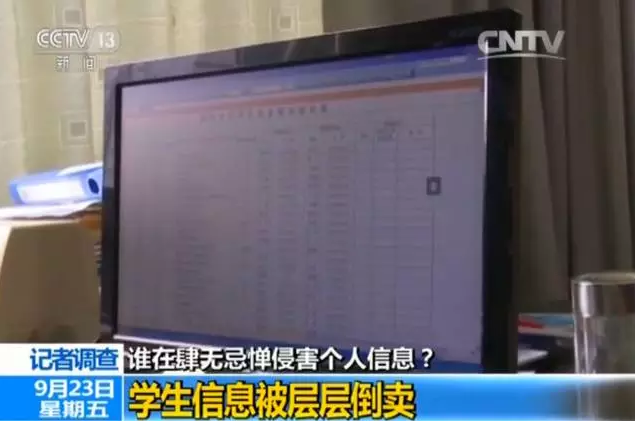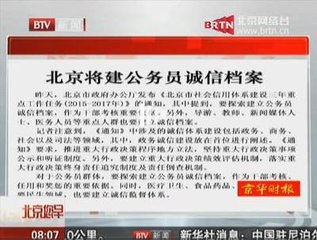连日来,一场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式治理,在深圳轰轰烈烈展开。8月25日,深圳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该局正在与多家征信机构联合建立深圳交通参与者征信体系,意将交通违法与个人 ...
连日来,一场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式治理,在深圳轰轰烈烈展开。8月25日,深圳市交警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该局正在与多家征信机构联合建立深圳交通参与者征信体系,意将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贷款、买房等挂钩,以此遏制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8月30日《法制日报》)
将闯红灯与信用挂钩,深圳并不是首创。今年年初,广州已经率先实施,但消息一经公布,就遭到了人们“道德绑架”的质疑。也就是说,闯红灯作为一种交通违法成本,已然受到了与其相对应的处罚,又何必再通过贷款、买房等代价来惩罚呢?这不仅是“重复执法”之争,更重要的是它显然在昭示着一种执法方向,即靠重罚来规训公众的“日常平庸之恶”。
让违法者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肯定能在相应领域遏制公民的违法行为,但问题在于,执法效果掩盖不了执法手段的不正当性,放置于此来说,用个人信用记录的方式来治理闯红灯虽是创新,但这两者又有何必然联系呢?
作为一种交通违规行为,闯红灯与“信用”简直不搭边儿,它只是一种“小恶”,而“小恶”就应该有其相对应的处罚规定,而不是在此基础上,让其付出“罚一赠一”的代价。抛去“重复执法”的争议不说,单就对这种“小恶”的治理逻辑来看,我们之所以要反对用贷款、买房等个人利益来绑架闯红灯等“小恶”,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很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被合法地侵犯。
是的,假如闯红灯可以影响到个人在其他领域的切身利益,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之恶”实在是多了去了,践踏草坪算不算?公共场合抽烟算不算?随地吐痰算不算?
按照对闯红灯的治理逻辑,如果诸如此类“小恶”都可以将其纳入诚信记录,进而与其他领域的个人利益挂钩,推演下去,简直就是一种无休止地变相“株连”,而将各个领域打通的那座桥梁就是所谓的“信用平台”。
闯红灯本来就与个人信用无关,却硬是将两者绑定在一起,谁能说它是合理的呢?这并不是社会公共治理手段的创新,而是对公民权利的变相压缩,在一个日渐形成的公民社会当中,无疑显得格外地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