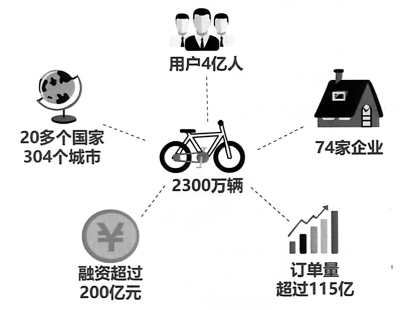秦晓鹰的文章“社会失信是发展之癌”(见六月七日本版),针对许宗衡“双规”前所表现的“道具”面孔,揭示了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而且是癌化的“社会失信”的共性问题。作者疾呼:“社会失信,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本人和秦晓鹰一样,对这种“社会失信”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感到揪心、忧心、担心。事实已摆在眼前,执政党能拿出什么“高招”来防止和扭转这种滑落的势头呢?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主要是谈及以下命题: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三是权力的“公仆”性质;四是思想方法。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反馈作用和相对适应作用始终是矛盾的统一体,它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互为因果关系。这是我们观察社会发展中出现矛盾的锁匙。
建有效权力制衡机制
中国在1949年的革命,是要建立所有制的新体制,但因为教条主义的顽固性,并未能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而在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模式中,削弱或轻视民主因素的积极和促进作用,权力逐渐向“集中”靠拢,加上封建主义传统的延续性及领导人思维方式脱离了客观实际,使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建立的具有“崇高理想”的社会,并没有真正行驶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而在后期的反思中,也缺乏深层的剖析和全面的创新。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市场经济作为解放生产力先导,它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致富光荣”启动了“文革”当中被压抑的私慾。当这个潘朵拉盒子被打开的那一瞬间,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不顾一切的“财富加速积累”的快车道。其它的社会改革、包括应该配套的政治改革被撇在一边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种种不公平正义和失衡现象,都是这个原因而导致的后果。目前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实际上是以纠偏而逐步走向创新;而“和谐”,是防止发生“革命”、避免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方式,以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其中也包括“第二次分配”。这当然是一个艰巨的“深化改革”工程。目前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有优秀的政治质量和智能去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的更高台阶。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因为“看得清楚”,才能以互动的方式,以忍耐和努力来共赴时艰,创造新的辉煌。关键就是两个字:“信心”。
以法制观念约束自己
政治改革的中心点就是权力的性质、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衡问题。中国可以拒绝多党制,拒绝三权分立,但不能拒绝对权力的制衡。它可以用现存体制内所能使用的“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制衡,包括制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由上而下),包括媒体的监察作用、网络作用(由下而上),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权力观念的彻底改变,以“做人民的公仆”为荣,以“做人民的主人为耻”,而中国的公民,要树立法制观念,不仅是对上的,也是对自己的。
“文革”期间,用“老三篇”作为“天天读”的“早请示,晚汇报”到底有多少成效呢?中国目前需要什么样的全民道德规范呢?如何打造呢?如何变成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为呢?一个处处是以“惟我主义”而生存的社会,就是“社会失信”的根源。
汶川地震唤醒了中国人的“利他主义”,温情和良知闪烁著人性的光辉。问题在于,这光辉能永远照耀中华大地吗?我们需要在“失信”与“光辉”之间,去做更多的思考。尤其是应从哪里里做起,问题的中心点在哪里里?这是很多关心中国命运的爱国者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秦晓鹰在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是的,失信并不单独属于不健康的市场秩序,它更属于一个管理、法律和教育失范的社会。失信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混乱、人心松散、腐败横行、公众遭殃,也必然会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应该像应对经济危机一样,去正视社会失信问题。应该像抓经济振兴一样,去好好培育、呵护已经岌岌可危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