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教育部推动的高中新课程改革迄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新教材整体上是令人鼓舞的,它分系列集中学习的编写法,有利于学生在高中学习的黄金时间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也赋予了教师教学更大的灵活度。从语文单科来说,选修课本涉及中国古代、现代与外国诗歌
由教育部推动的高中新课程改革迄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新教材整体上是令人鼓舞的,它分系列集中学习的编写法,有利于学生在高中学习的黄金时间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也赋予了教师教学更大的灵活度。从语文单科来说,选修课本涉及中国古代、现代与外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还有中外人物传记、新闻写作等等,个人认为这对学生的教益胜于大学语文公共课。
但是,旧教材由专家精心编撰,且经过中学教师多年实践检验;新教材中的有些问题则亟待修正。以人教版为例,必修系列多为与旧教材共有的经典篇目,尚好;选修系列,譬如《中国诗歌与散文欣赏》,其编写体例,既不按照年代,也不按照体裁,而只是加上一个松散主题,将数篇诗文捏合在一起。选文的代表性也有商榷的余地。清词一首而选纳兰性德,恐怕是流风浸染;清诗一首而选黄遵宪之《今别离》,也多少有点古怪。
如果说编写的优劣,还属见仁见智,那么,常识性的错误则应尽量避免。这问题在《先秦诸子散文》课本与配套教参里,似乎格外严重。基础教材固然可以汲取最新研究成果,但不宜太积极于“尝鲜”,而仍应依循为多数人接受的旧注,尽管也应扬弃确有问题的部分。譬如《论语·颜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课本对最后一句话如是翻译:“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但假如人民不信任政府,那么政府就不可能立住脚。”(2006年12月第二版,p21,注解⑨),据此,则“信”解释为“信任”。
但是,“自古皆有死”与“民无信不立”之间明显构成转折关系,解释为“信任”很难讲通。“去兵”“去食”还让百姓“信任”政府,这合乎人情吗?
个人理解,倾向于取“信”的本意,也就是诚信。从后文来看,孔子讲的是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子贡才会问他“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所谓足食,是发展经济;所谓足兵,是发展国防;而诚信,则是孔子最重视的教化。经济发展,国防稳固,百姓诚信,这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如果不能做到,“兵”可以首先去掉(儒家本来就反对武力),再不行,“食”也可以去掉,可是这个“信”却是立国之本、立身之本,死都不能丢的。朱熹《论语集注》:“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这个解释是贴合的。孔子主张“君子务本”,所以他把“信”这个“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这样,“自古皆有死”与“民无信不立”之间的关系就豁然贯通了。
如果说这一处解释还属有争议不妨两存的话,“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第26页注解⑤把“知者利仁”翻译成“算计得精明的人利用仁”,则不可原谅。从字义讲,“知”同“智”,“利”是使动用法,“利仁”即“以仁为利”;把“知者”翻译为“算计得精明的人”,“利仁”翻译成“利用仁”,这是学生也不会犯的常识错误。从句义讲,孔子教导弟子以仁为牟利的工具,这种“创见”也委实太过惊人了吧?
那么,“仁者安仁”,该作何解释呢?朱熹说:“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惟仁者则安其仁而无适不然,知者则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盖虽深浅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夺矣。”他的意思是,不仁的人失去“本心”,久处穷困则胡作非为,久处安乐则过度放纵。而仁者安于仁,无论到哪都能坚守;智者认为仁有好处,也不会改变操守。前者境界更高一点,但二者都不易因外物而动摇。颜渊能够“陋巷箪瓢”却“不改其乐”,这就是“仁者安仁”的典范了,所以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其余弟子虽然达不到这种境界,但能从理念上认同“仁”而坚守,同样难能。
不但注解有问题,某些课后习题的设置以及教参的讲解也有问题。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断然不能依赖教参,但恰因教改,一般中学教师在对新教材摸索熟悉的过程中,对教参的依赖程度势必超过从前,不少配套练习答案的编写又以教参为依据,如此必然误导学生。
第12页课后习题第一题题干如下:“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如何评价这两种处世方式?”
这道题设题思想根本性错误。设题者将《孟子》原文截去一半,抽出末句,而问孔孟处世方式有何不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孔子推行自己主张死而后已,孟子则“滑头”一点。教参的解说是:二者都以修身为立足点,“但是孔子对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显得更为执著”。但孔孟的“处世方式”难道有什么根本性不同吗?不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栖栖惶惶,席不暇温?
《孟子·尽心》篇中原文如下: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整段话的重点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即无论贵贱穷通都要坚守道义,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理念是相通的。否则,孟子不是成了“曳尾涂中”的庄子了?
更让人惊骇的是第21页课后习题二。题干说孔子虽强调“信”却不是片面地无条件推崇信,引《史记·孔子世家》“要盟也,神不听”倒没问题,但另一则引《子路》章“何如斯可为之士矣”,却偏偏截去最后一句话,并且把“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翻译作“言语一定要诚实,行为一定要坚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知道贯彻自己言行的小人啊!”教参答案,复引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为证。照此说来,难道孔孟都认为,人不必守信,守信的反是小人?
其实,回到论语原文,孔子对“士”的要求是分层次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是治国平天下之士;“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是齐家之士,“言必信,行必果”仅仅达到“士”修身的基本要求,孔子并非否定言必信行必果,而是单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还很不够呢。但这也比那些“斗筲之人”的“今之从政者”来得高明。所以最后一句话万万省略不得。而孟子那句话重点是放在“惟义所在”,也就是“义”是衡量行为的更高准则。这和《里仁》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相通的。
我在这里仅仅摘取了前几课《论语》部分例子,《论语》文字朴素,多口语,又作为儒家典籍,前人注说详尽,课本编写者大有依傍,却发生这么多问题,斯亦勇于“尝鲜”之害欤?时下“经典”重又成为流行,文化明星高踞讲坛,民间注家热行坊间,但编写课本是极为严肃的事情,将直接影响全国众多中学生,宁可“保守”一点,审慎一点,以免谬种流传。子贡说“言不可不慎也”,承担传承文化重责的出版人,尤其不可不慎。希望能早日对教材进行更严密的审核与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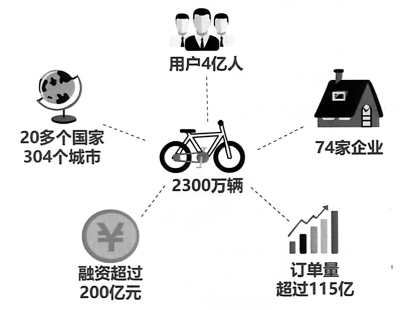










监督方式防骗必读生意骗场亲历故事维权律师专家提醒诚信红榜失信黑榜工商公告税务公告法院公告官渡法院公告
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政府信用网站信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技术研究市场研究信用评级国际评级机构资信调查财产保全担保商帐催收征信授信信用管理培训
华北地区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北天津北京华东地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华南地区广西海南福建广东华中地区江西湖南河南湖北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辽宁西北地区青海宁夏甘肃新疆陕西西南地区西藏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