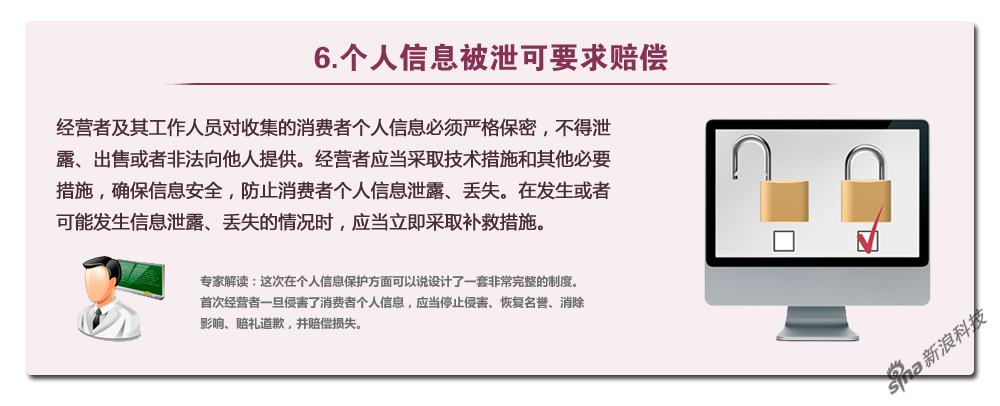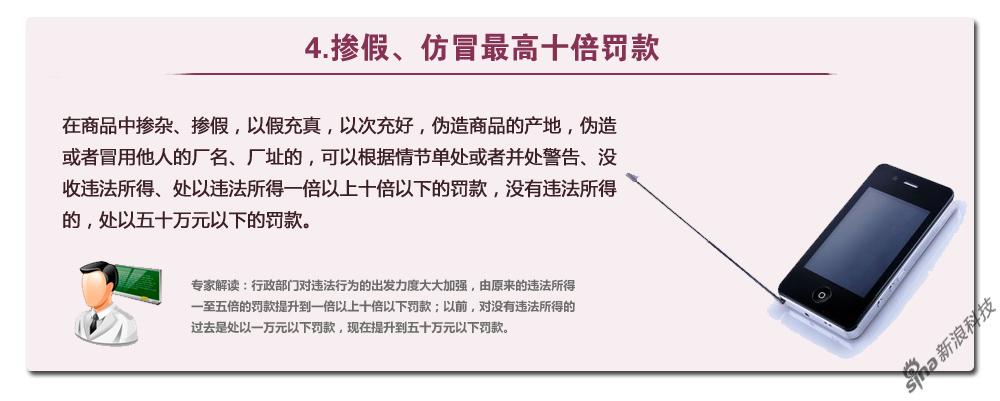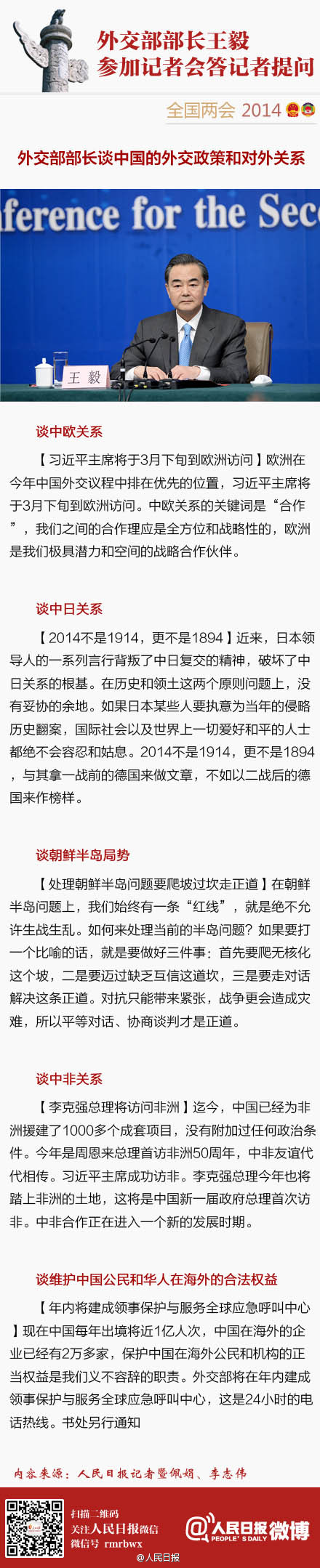我国社会信用的现实思考
来源:网络转载
2008-07-14 08:47:56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这就意味着“孝”是“忠”的基础。笔者在《在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中曾谈到:“父为子纲虽然包括个体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关系,但这不是父为子纲的要义所在,因为父亲对成年已婚儿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维持的根本。”实际上,父亲对未成年儿子的控制是自然而无需强调的。
尽管“情”是家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但“信用”依然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信用关系的从属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下对上不讲信用,则为不孝、不义和不忠,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为社会所不容。而上对下不讲信用虽然不为社会所提倡,但往往为社会所宽容。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注意,这里的“义”不是指“情义”,而是指“道义”。第二,信用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曾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讲信用比喻为能够行驶的车,不也是强调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与朋友交往吗?
信用关系的普遍化有赖于经济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本身对自然经济的从属性质决定了信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从属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从而最终使个人、而不是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分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我们可以一推了之的东西。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正如一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总是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一样,不考虑中国的过去就来讨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就等于把一个成年人当作婴孩看待,结果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婴孩。
家族社会的阴影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封建家族在战乱中不断瓦解,但家族的组织形式,家族的思想观念,家族的道德规范等等依然存在着。
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一直沿袭“讲成分、查三代”的作法。这是为什么?阶级是按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为什么要查“三代”?这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这种作法等于把个人仍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虽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说,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连”。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对于一个刚从家族社会走出来的新社会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有什么不对,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对,而是社会的不对。在家族社会,个人属于家族,这就好像蜜蜂属于蜂群一样。一人遭殃,满门不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本能地将一切组织家族化,或一切组织本能将自己家族化,这是即使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所谓企业办社会,所谓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每个企业都力图把自己办成一个独立王国,即一个自给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会。因为只有自己靠得住,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计划是为国家完成的,与自己无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仅决定于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实际上也决定于计划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协调性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试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强调内外有别,一个组织排斥另外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排斥另外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区排斥另外一个地区,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进行协调,但高层政府官员又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始终大公无私呢?当然,组织家族化自有其温馨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至今留恋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国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由“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激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统论及各种个人崇拜的口号被并非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价响,再次显示了传统家族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场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促使中国人从此确信“猫论”才是正确的。
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个人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但是,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发奖金,人人有份,拉不开差距,结果还是“大锅饭”。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行业之间,而这种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
所谓“大锅饭”,其实正好来源于“大家庭”。“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气势恢宏,但培养出来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大家庭”内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公有制企业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内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铁饭碗,领导坐的是金交椅。从外部看,国有企业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权利就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的集体企业不如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民不如工人。
市场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费品市场,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似。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调拨;虽然名义上有银行,但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统存统贷”,而且信贷计划由实物计划决定。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实际上不存在。只有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分家”?
在农村,问题在开始时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分了“人民公社”的家。家庭,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枯木”终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民公社的凝聚力都无法与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经济组织,更何况人民公社。
在城市,问题在一开始就异常复杂,因为企业无法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不是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实际上,即使能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承包、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
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样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领导“让贤”呢?实践表明,相当部分的所谓“能人”其实都不过是骗子和“硕鼠”而已;与“让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肆无忌惮的“跑官”、“要官”。
中国古来就有“父母官”与“子民”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国家化为家族,再进一步化为家庭的幻想。为官要爱民,如父母爱子女;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实际上,一旦超出个体家庭的范围,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是随着家族的扩展而降低的。要求一个家族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家族成员,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职工呢?如何才能保证企业领导者公正无私呢?
遗憾的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家族制度,它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帮助。家族的稳定靠的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现在我们说论资排辈不好,但对于家族来说,严格遵循按辈分、长幼形成的等级是家族稳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国家的皇帝在确定接班人时,往往也不敢轻易废长立幼。家族内部讲和为贵,讲一家子其乐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别则决定于辈分和长幼,赏罚难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也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就正是这样吗?当然,王熙凤还有其自私弄权的一面。不过,在她看来,不以权谋私则她对家族的贡献就没有得到回报,就对不起自己。这其实又何尝不是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能人在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或之后贪污受贿时的想法呢?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选举制,有竞争力的家族领导者都难以通过选举产生,这是由家族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能盲目迷信选举制。第二,家族既难以产生和支持对家族有利的强者,也很难抑制对家族不利的败类,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必须要有耐心,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坚强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数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外来压力有利于团结则有利于改革。这正是家族体制本身的悲哀,而我们现在仍强烈地感受着这种悲哀,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其实仍在家族阴影的笼罩之下,挥之不去。
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动力但缺乏制约的改革结果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企业的领导者可能既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东的利益,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为“穷庙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发横财之后远走他国。实践同时表明,由于控制链条太长,国家很难对无数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企业内部事实上存在的等级体制或准等级体制(因为需要加强领导而成为必要)又使企业职工对领导层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不可能,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国有资产在职工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流失的原因。总之,“家”分给谁?对于没有真正的家庭、也无法由真正的家庭来作为承担者的经济组织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结果就表现为产权不清。
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
“分家”没有完成,或者说,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又何来的信用危机呢?当人们谈论信用缺失的时候,似乎把信用关系在过去的普遍存在作为前提。其实,中国在过去并没有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改革的任务正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在“情”、“义”和“忠”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信用关系总的来说是受到维护的,这实际上由市场存在的必要性所决定。“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碳值”的情况肯定存在,但不可能总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市场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明确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受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
首先,借助于市场的个人致富受到鼓励。市场、特别是由不成熟市场所天然具有的投机性而产生的巨大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马克思说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对货币财富的疯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视一切,信用观念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观念本来就不够强大,不讲信用在很多场合仅被视为“赖”而已。时至今日,当人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羞惭呢?
产权不清为失信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公肥私很容易发生,也容易得逞,虽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为失信者要么损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业的领导者违背对国家的承诺,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借了国家银行的钱不还;要么以欺骗的方式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不以强制手段直接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人们对不讲信用的现象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家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从一楼一直安到顶楼的沉重的防盗栏不正在向我们述说着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吗?假货也是消费者自己去买的嘛,因为人们或者可能不知道他们买的是假货,或者不得不买假货。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与种种不讲信用的社会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
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不讲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业领导、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个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国家的企业借国家银行的钱不还,对国有企业来说,似乎是应该的,而且在背后往往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业往往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政府官员索贿受贿,这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无秘密可言。因此,很明显,根源还是家应该分给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我们的某些代理人手中、即在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和某些相关的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而老百姓作为需要被加强领导的对象,又有多少可以作为的余地呢?
其实,不讲信用是现象,而本质是: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大家庭”真的面临危机了。首先,在各种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无端地变得紧张,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一句话,家族式的组织体制开始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各种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兄弟情义”已开始经受利益争夺的考验,下级对上级已开始“不忠”,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新的家族已经开始萌芽,即权力家族。人们崇拜权力胜过崇拜金钱,因为有权就不难有钱,有权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而仅仅有钱则可能难以有更多的钱。于是,在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中,我们看到“39岁现象”。时间是权力的制约因素,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在对权力的滥用中,我们看到“59岁现象”。
权力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控制系统或支配系统,因此,离开了支持者,就无法行使权力。在权力家族中,这个控制系统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因为被效忠的是位高权重的个人,是效忠者的利益来源。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从的关系。权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组织家族的权力中枢,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在社会下层,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开始出现,“义”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买马”旗帜。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中,圈内人相互“称兄道弟”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深思的。
家族的幽灵始终不愿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成,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家族的幽灵就总有藏身之地,或者说,家族的幽灵被人们所需要,或用于谋私,或用于自卫。但是,家族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发展来说却是严重障碍,因为不管是“情”、“义、”“忠”还是“人情”,它们都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相违背。当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大声呼唤“三公”原则时,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三公”原则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啊!
除了因产权不清而造成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渐进的模式对信用关系的建立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说,有控制、渐进的改革模式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选择才可能防止或减轻社会动荡,但这个选择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牟利,恰恰相反,它会在三个方面诱发和助长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原因很简单:
第一,既然要改革开放,控制就必须放松,必须对企业“松绑”。在法制不健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了发财致富的“硬道理”,“松绑”后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因唯利是图而置信用于不顾势在必然。
第二,既然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需要做试验,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全局的控制,但破坏了地区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不利于信用关系和信用观念的建立,相反,却会助长在中国本来就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和对特权的滥用。“搞关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场合还得以“搞关系”为基础,比如为争取成为改革的试点地区或试点单位而不得不上下打点,这就是特权普遍存在的证明,因为“搞关系”其实就是为了利用特权。
第三,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进行调整或纠正不当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但却同时也使得不讲信用的行为有充裕的时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不断地毒化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不少的人对不讲信用的行为习以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害者往往也自认倒霉。
中国信用财富网转发分享目的是弘扬正能量
关于版权:若文章或图片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源作者或者版权人联系我们(电话:400-688-2626 史律师)我们将及时删除处理并请权利人谅解!
相关推荐
国家发改委
2018-09-20 16:17:01